預(yù)測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曾經(jīng)是一件很輕松的事情:在學(xué)院改革前,評委必須在洛杉磯和紐約指定的電影院觀看所有入圍影片,然后才能就這個單元投票。這意味著話語權(quán)集中在那些住在這兩個城市、處于半退休狀態(tài)的老電影人手中,因為只有他們才有這樣的條件和精力。這個群體人數(shù)大概在六百左右,審美相對保守,喜歡老年/家庭/二戰(zhàn)歷史題材,基本上他們的喜好就能決定最佳外語片的歸屬。
與此同時,最佳外語片保留了自己的最大特色:從2007年開始實行的兩輪甄選制。這個制度可以用一個簡單公式來表示:N→9→5=1(每年N個國家報名,先初選九部,再提名五部,最終有一部獲獎)。外語片委員會每年會邀請400位評委來一起審片和打分,選出分?jǐn)?shù)最高的六部影片,再加上外語片執(zhí)行委員會自行挑選的三部,這九部構(gòu)成了初選的九強(qiáng)名單。之后再隨機(jī)邀請30位住在洛杉磯、紐約(去年起新增倫敦)的評委內(nèi)部討論,決定提名的五強(qiáng)名單。可以看到這個過程其實是非常盎格魯-撒克遜視角的,最終所有評委投票選出的其實是已被美國主流文化篩濾過的最佳外語片。因此在做提名預(yù)測之前,我們不妨先退后一步,回顧一下今年各國的申報情況,看能否從中梳理出一些世界電影的發(fā)展趨勢。

美國電影藝術(shù)與科學(xué)學(xué)院
今年共有八十一個國家和地區(qū)報名,但阿富汗的《烏托邦》因為有太多英語對白被取消資格,所以角逐明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電影只有80部。這其中包括76部劇情片、2部紀(jì)錄片(瑞士的《伊拉克人的奧德賽》和巴拉圭的《多云時分》)、1部動畫片(巴勒斯坦的《18個通緝犯》)以及1部短片合輯(新加坡的《7封信》)。今年只有巴拉圭是首次報名奧斯卡。中國大陸提交了《滾蛋吧!腫瘤君》,香港地區(qū)是《破風(fēng)》,臺灣地區(qū)是《刺客聶隱娘》,體現(xiàn)了華語區(qū)截然不同的選片標(biāo)尺。

《多云時分》
從今年最佳外語片的申報我們可以大致看出四個趨勢:
一、不同國家/民族的合作增加,電影呈現(xiàn)更多包容性。今年很多國家申報的電影,使用的都并非本國語言。法國的《野馬》是客居法國的土耳其導(dǎo)演拍的關(guān)于土耳其女性地位的寫實電影,全片沒有一句法語對白。橫掃以色列國內(nèi)電影獎的《瓊恩老爹》主要語言是波斯語,因為該片講述的是集體農(nóng)場中一個伊朗移民家庭的兩代沖突。瑞士提交了一部3D紀(jì)錄片《伊拉克人的奧德賽》,回顧近代伊拉克的民主夢是如何被異國入侵和獨夫強(qiáng)權(quán)碾碎的,主要使用阿拉伯語。愛爾蘭同性電影《維瓦》發(fā)生在說西語的古巴,主角是一個做著變裝夢的哈瓦那同志美發(fā)師。澳大利亞的《雷龍之箭》則把取景地直接移到了喜馬拉雅山麓的不丹村落,描繪當(dāng)?shù)胤忾]生活被打破后的變化。
如果說英語國家是受奧斯卡外語片的語言限制,不得不提交跨國電影的話,法國、瑞士、以色列這些非英語國家的主動選擇就很耐人尋味了。由于奧斯卡規(guī)定“申報國必須確保該國主創(chuàng)人員的署名應(yīng)占影片的多數(shù)比例”,這意味著像《野馬》這樣的電影,雖然從導(dǎo)演到主演到故事全部來自土耳其,但骨子里其實是被認(rèn)定為“法國制造”的,由法國深度介入該片的拍攝并且具有藝術(shù)上的貢獻(xiàn)。而中國提交的《狼圖騰》被學(xué)院打回,則顯示了這種跨國合作的惰性風(fēng)險:如果一國只是簡單的出資金、演員、場地,沒有“藝術(shù)貢獻(xiàn)”(劇本、導(dǎo)演、剪輯、攝影...),這樣的電影是不能代表該國電影工業(y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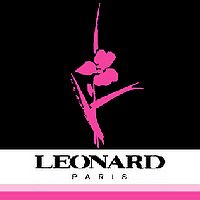



 粵公網(wǎng)安備44030702000122號
粵公網(wǎng)安備4403070200012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