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東學為《時尚男人裝》雜志拍攝了一組寫真。墨鏡后的他眼神犀利,硬漢氣十足;機車上的他手持香煙,頗有雅痞范兒。除此之外,李東學還接受了雜志的深度采訪,他坦言自己在“果郡王”之后,沒有再接同類角色,這樣的行為或許在他人看來很“脫軌”,錯過了大紅的機會,但他只沉溺于戲,只想忠于自己的初心。
采訪原文如下:
在部隊大院長大、踢過足球、計算機系科班出身……但最后,他成了一位演員。趁早忘了那個多情的 “果郡王”,接下來要上映的《鋼刀》才能看到他真正的男性荷爾蒙。就像他為我們拍這組大片時偶然流露的那樣:堅硬,意味深長。脫軌,沒被這個世界一巴掌拍死,又活出了自己的體系。這事兒,真的很爽。

兒時那些破滅的夢想
在中國足球還屬于郝海東的時代,“調皮搗蛋”的李東學曾當過一陣子足球運動員。在部隊大院長大,父親是海軍航空兵,那個年代的記憶是紅色的,他夢想自己有一天能進入國家隊,“踢出亞洲,走向世界”。每天早上聽著軍號起床,一輛大巴準時把這些大院孩子送到學校,家里準備的盒飯在中午按時加熱,生活運轉得如同一套機械系統。學校里有游泳池,甚至還有機場,看夜航是最過癮的,每到重要節日還有禮物……在全國人民還憑著糧票過日子的時候,李東學就已經偷偷喝過老爸的香檳了。可能這樣的童年,更難生產循規蹈矩的人生。
“當然也有叛逆,因為父母總不在身邊,大部分時間跟著外公外婆。”當他和我說起這些時,樓下的哈雷摩托車發出轟隆巨響,這或許給了他一點回憶的靈感。
“我想過開飛機,后來放棄了,因為個子太高——駕駛戰斗機對身高是有要求的。”他很平靜地說著那些夭折的夢想,“對,我少年時代的夢想一直都在破滅。坦白講,直到上電影學院之前都在破滅。”
高中畢業,父親讓他考軍校,他不從,考了當時最熱門的計算機系。畢業時,恰逢第一輪互聯網泡沫破滅,中關村擠滿了找工作的計算機系畢業生。無路可投的他一邊在新東方學英語,一邊偷偷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這事兒,他一直瞞著爸媽。
那時的他20 多歲,沒什么方向感,只是覺得當演員是件挺有意思的事,還有那么點虛榮心,“演員嘛,Easy money !”他說。
顯然,那時的他還不知道什么是偉大的表演。在電影學院的那些日子,他慢慢懂得,“演員是非常難的職業,越簡單的東西越難。它看不見摸不著,需要感覺,需要閱歷,還需要非常強的感受力。它是創造,會讓你覺得這是一個需要不斷創造的熟練工種。當然,你還需要那么點運氣。”
從始至終,都是個爺們兒
“我干過的所有事都非常爺們兒。”
“爺們兒”是李東學非常喜歡的字眼兒,他讀過王朔的《頑主》,看過香港的《古惑仔》,在拍攝這組大片時,他也玩得很high,靠著摩托車,拎著啤酒瓶,冷不丁丟出一道冷冽的眼神……有點像詹姆斯·迪恩,不帶一絲煙火氣,聯想起《甄嬛傳》里的果郡王,你會覺得他只是缺了一根被點燃的引線。
參加了兩次高考的李東學進入電影學院后還是有點心虛,“到了這里發現自己什么都不懂,迷茫、崩潰,這太恐怖了,感覺弄不好就是人生的終點。怎么辦?只能拼傻力氣了!”為了形象他從170斤減到146斤;別人放寒暑假,他貓在宿舍里瘋狂看片兒;系里安排的周六日選修課他也一節不落。“用傻力氣當然很傻,但它讓我明白,這就是意志,你不信它就是不信自己!這也是一種血性,能壓制自己的欲望,能控制自己。”
上電影學院的第二年,李東學就不再問家人要錢了。他拍了很多廣告,收入體面,然后拍了自己的第一部戲,并時不時給父母一些錢貼補家用。其實家里也不缺什么,他就是覺得,爺們兒嘛,就得為家里干點什么!
或許,這些人生的養料來自于他那段“足球運動員”的經歷。他說,“這就是比賽。有時,比的不是你的能力有多少,而是你是否在堅持。真正的爺們兒,不是外面的樣子,而是內在的堅韌和自制。面對恨,你是什么樣的;面對難,你是什么樣的;面對誤解、詆毀,你是什么樣的……我覺得只有這些東西,才能體現一個男人真正的質感。”
在采訪時,他會隨口說出一大串電影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無論是背景、作品,還是演技都如數家珍,他們大多是好萊塢里的硬漢,比如羅伯特·德尼羅、馬修·麥康納。但平時的他溫良平和,沒有過分的野心,他的棱角是向內的,像極了那句俗不可耐的廣告語:男人,就該對自己狠一點。
在“果郡王”之后,李東學演過將軍、錦衣衛、律師、公務員,甚至還有偶像劇里的反派人渣。對于演戲,他有股晚成的自信,“無論是生旦凈末丑,工農商學兵,我都能駕馭。如果還不能達到生命的厚度,那我就有意識地拉開寬度。”接下來,我們聊到了影片《鋼刀》。這部電影的梗概非常簡短——講述了一個戰地絕境、兄弟相殺的故事。這讓它看起來有點像《太極旗飄揚》,但導演阿甘顯然想把《鋼刀》拍得更炫更酷。它的視覺由昆汀· 塔倫蒂諾《罪惡之城》的攝影師和技術團隊操刀,視覺風格與《罪惡之城》如出一轍,不過前者是未來的城市,而《鋼刀》則是半個多世紀前的荒野戰場。
李東學在阿甘的工作室里看到這部電影的Demo就被吸引住了,“(這部電影)細節和情感做得很好,尤其是特效,非常過癮!”
為了過癮,李東學拍了差不多兩年時間。《鋼刀》對于中國電影來說,充滿了實驗性。它在數字化拍攝方面,根本沒有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第一條測試片就拍了一年。阿甘在一次采訪中說道,“必須一邊拍一邊測試新的技術難點。在中國,從未有人參與過如此大型風格化、特效電影的制作,每走一步,都是一次探險。”
5 年,1800 多個特效鏡頭,500 多名數字藝術家,五易其稿,一群勇猛的人做了件堅毅的事。“整個過程像拉鋸”,中間經歷過什么,李東學并未細說。在電影里,他飾演弟弟,留著一頭板寸,穿著十幾斤的大棉軍服,槍上頂著刺刀和“哥哥”(何潤東飾演)拼命。
“拍這個戲,我感覺又回到了電影學院,那時大家排練一個通宵都不累。這次,我們經常連軸轉24 小時,都跟打了雞血似的。這些年拍戲,還沒有哪個劇組讓我經歷過這個。”
每天,李東學醒來第一件事就是長達3 個小時的化妝。因為臉上的傷疤要畫一層粉底,畫完了還要往臉上抹泥,再用小牙刷刷出充滿顆粒感的泥漿,之后還有血漿。“戰爭戲就是這樣,大家都在扛著、撐著,”他停頓了一會兒,“不管結果怎樣,都意義非凡,至少大家都high 了。”
對于這出戰爭戲,這個從部隊大院里長大的男人自然有股很硬的情感在里面,“以前覺得自己是個街頭賣藝的,彈個琴賣個曲兒啥的。拍完這個,覺得整個人都不一樣了。《鋼刀》的寓意,是比鋼還強,比刃還利,取人頭顱,出生入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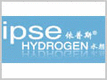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44030702000122號
粵公網安備44030702000122號